本帖最后由 海尔罕 于 2025-7-11 20:39 编辑
编者按:《多情雪——舒柯中短篇小说选》后记中,苏家澍先生以幽默自嘲的笔调回顾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。他从童年读《水浒》的痴迷,到成年后在不同领域“越俎代庖”的写作经历,再到如今对小说创作的敝帚自珍,展现了一位作家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。他自谦作品无派无流,实则扎根于湘南大地,饱含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深情与眷恋。这些作品不仅是文学创作,更是他对时代、对生活的爱憎与评判,是他无悔的笔耕成果。
读小说是一辈子的嗜好,从小至今,乐此不疲。小时候借得一本绘像《水浒》,就着如豆油灯,掭亮灯芯,如饥似渴,囫囵吞枣读完。念大学时,嫌图书馆准借书的数量太少,便将急于先睹为快的图书如同腰缠集束手榴弹一样插满腹前背后,“偷”出馆外(读后完璧归赵,请勿见疑)。芝麻官当了多年,翻开每期《新华文摘》等杂志还是先看小说。即使住进医院被滴注瓶、软管“吊”住,得空的手擎着的书卷大多是小说。究其实,不是为了消遣,实实是一种惯性,一番思念。
我曾说过我是杂家,之所以杂,是如鲁迅先生所言“遵命”的缘故。“WG”前在剧团当编剧,自然要编剧。八十年代初到地区(市)文化局供职,为了在经常举行的全省、全国各类戏剧汇演中不致名落孙山,自己也难免越俎代庖写写剧本。后来转任市宣传、广播电视系统,顺理成章地又问津于电视剧、广播剧、电视专题片。每逢现实级几周年、历史级几十周年庆典总要奉旨写点什么。写小说却只有几年的缘分。那是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的四五年当中,精神枷锁卸下了,也不必非写规定题材、规定体裁不可,于是乎便在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领域信马由缰,四下游击。今年春节前搬家,自然翻箱倒柜,将尘封多年、散见于各地报刊的文稿翻检出来,分类归档,自认为小说者,竟也有几十万字。敝帚自珍,结集付梓的念头油然而生。如今小说集即将面世,想想无非是一番回首,几分自勉,如此而已而已。
放眼当今文坛小说界,流派林林总总,种类形形色色,评论纷纷纭纭,实在叫人读之眼花缭乱,思之莫衷一是。翻阅鄙人拙作,似乎入不了什么流,够不上哪一派,也未曾刻意师从、野心创造,多半是目有所睹,心有所感,要流之于笔端,而短诗、散文盛之不下,纪实文体难以曲尽的,便漫溢成为小说。如果有幸归属于民族的、现实主义的麾下,自当视为褒奖。
我的家乡是一座汉朝即为县治的湘南古城。那条湖南唯一汇纳于珠江水系的武水,滋润了我童年、少年的梦里情思。大学毕业以后,我曾经在井冈山下一个山城工作多年。我钟情于故乡和堪称第二故乡的那方热土,我谙熟那里的风土人情、方言俗语,曾穿梭于湘赣边境的瑶汉村寨、山乡小镇,在镶铺小路的青石板上考究过远古的化石、飘渺的神话,辨认过挑夫的草鞋印痕。在松鼠、猕猴出没的羊肠小道,寻觅过巨人的足迹,谛听过历史的回声。那云雾缭绕的山林,那溪流淙淙、银瀑喧飞的峡谷,那樵夫、村姑高亢撩人的山歌俚曲,机智诙谐的传说掌故,至今仍然音犹在耳,铭记在心。湘南那飞檐斗拱、聚族而居的村落,那茅檐低小的排杉土屋,那采药者、挖蕨汉、造纸人蜗居的深山寮棚,是我人生真正的课堂,身为农夫山民的父老兄弟是我真正的老师。在书声琅琅、粉笔扬尘的校园,有我的师长、学友、同人、弟子。他们的音容笑貌、心态神情,历历在目,可描可绘。这些就是我笔耕的泥土、苗圃,就是小说的情境和人物。我的作品忠实于那个时代,流露了我的爱憎和评判,对此我是无悔和聊以自慰的。
这部集子里作品的“文龄”都二十岁上下了。八十年代以来,神州大地改革大潮汹涌,社会各个层面、政治经济领域、人际关系、思想观念的坐标取向都发生了巨大的、深刻的变化。我的生活自然也有了新的积累,新的发现。可惜的是我还来不及去咀嚼,去形之于文。社会底层的体验,政界官场的阅历,应该说,这是生活赋予的的富矿。以后肯定还要写点什么,兴许能更专注于小说的写作,弥补一些留下叹惋的遗憾。说不准,还会追逐点什么新潮,谁知道呢? 廉颇老矣,尚能“写”否?(1998年7月12日 于郴阳)
附言:《舒柯中短篇小说选》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,舒柯即苏家澍笔名。 | 





 窥视卡
窥视卡 雷达卡
雷达卡
 发表于 2025-7-11 16:59:58
发表于 2025-7-11 16:59:58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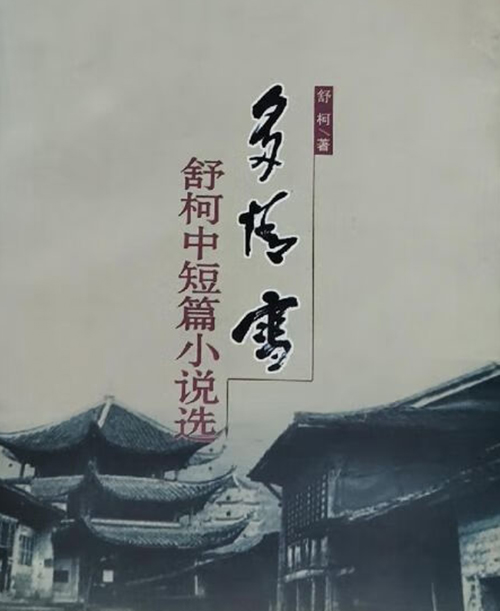
 提升卡
提升卡 置顶卡
置顶卡 沉默卡
沉默卡 喧嚣卡
喧嚣卡 变色卡
变色卡 千斤顶
千斤顶 照妖镜
照妖镜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