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|
本帖最后由 海尔罕 于 2025-11-9 15:54 编辑
避暑山庄的门槛委实是高,我用力抬了左脚,又抬右脚,才勉强跨了过去。尽管导游反复提醒不能将脚踏在门槛上,那黑黝黝的门槛还是被无数鞋底磨得发亮,倒映着游人的影子,明晃晃的,仿佛是在嘲笑我这个南方人的拙笨。
三十二度的气温,百分之八十九的湿度,这哪里是什么避暑胜地?分明是我的故乡武汉,只是少了些火炉般的燥热,多了些承德特有的沉闷。我向导游抱怨:"这般天气,皇帝何以来避暑?"导游是个精瘦的承德本地人,面皮晒得黝黑,闻言只是笑笑:"您,且往里走。"
走便走罢。人群如潮水般涌动着,我夹在其中,像一条不情愿的鱼。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,衬衫黏在后背上,很是不爽。忽然,一阵微风拂过,带着松柏的清香,我抬头望去,只见远处湖面上浮着一层薄雾,如梦似幻,倒是与昨日在武烈河畔所见有几分相似。
昨日黄昏,我确是在武烈河边见过这般景致。那时刚在大清花饺子馆用过晚饭,东北菜油重味浓,吃得我满头大汗。走出门来,却见河面上升起厚厚一层雾气,将两岸的灯火都裹了进去,朦朦胧胧的,煞是好看。我原以为是人工造景,便问了一位在河边纳凉的大姐。
"这雾是打哪儿来的?"我指着河面问道。
与我年龄相仿的大姐摇着蒲扇,操着一口浓重的承德口音:"自然有的,不常见哩。昨儿个下了雨,今儿个又晴了,才生出这等雾气来。"她稍作停顿,又热心地说:"明儿个你们要去避暑山庄吧?赶巧了,那儿湖上有时也会起雾,比这还好看哩!"
此刻站在避暑山庄内,我才明白大姐所言非虚。那雾气从湖面上升腾而起,渐渐弥漫开来,将远处的亭台楼阁都笼罩其中。游人如织的嘈杂声似乎也被这雾气吸收了,变得遥远而模糊。我的衬衫仍然黏在身上,心却奇异地静了下来。
导游不知何时已走到我身旁,指着那雾气说:"这就叫'烟波致爽',是山庄七十二景之一。乾隆爷有诗云:'烟波致爽搴珠箔,月镜涵虚挂玉钩',说的就是这景象。"
我望着那雾气出神。二百多年前,那位十全老人是否也曾站在此处,望着同样的烟波?那时的雾气,可也是这般模样?历史书上的乾隆皇帝,是个好大喜功、附庸风雅的君主,他六下江南,挥霍无度,留下无数风流韵事。但站在这烟波之前,我忽然觉得,那个活生生的、会为一场雾而作诗的乾隆皇帝,或许比史书上的形象更为复杂。
人群又开始移动,我被裹挟着向前。转过一道回廊,眼前豁然开朗——一片开阔的湖面,雾气更浓了。导游说这是"澄湖",湖中有个"烟雨楼",名字取自杜牧的"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"。我眯着眼睛望去,果然见一座二层小楼在雾中若隐若现,宛如水墨画中的景致。
"这楼是仿嘉兴南湖烟雨楼建的,"导游解释道,"当年乾隆南巡时见了,甚是喜欢,回来就命人照着样子在这儿也盖了一个。"
我不禁莞尔。这位皇帝老爷,倒是个痴人。喜欢一处景致,便要原样搬回家来,活像小孩子见了心爱的玩具,非要据为己有不可。可转念一想,若非这等痴性,又哪来今日我们所见之避暑山庄呢?
雾气渐浓,竟有些凉意袭来。方才还嫌闷热难当,此刻倒真应了"烟波致爽"这四个字。我似乎明白了皇帝为何选在此处建山庄——热河之地,暑天固然炎热,但有水有山,早晚温差大,兼之湖面常有雾气蒸腾,反倒比北京城里那密不透风的暑气要清爽得多。
导游引我们来到一处名为"万壑松风"的景点。但见古松参天,枝干虬劲,想来都是几百年的老树了。松针在微风中沙沙作响,与远处湖上的雾气相映成趣。我靠在一株古松旁,树皮粗糙的触感从掌心传来,带着岁月的痕迹。
"这些松树,大多是康熙年间种下的,"导游说,"您看那棵,传说康熙爷亲手栽的呢。"
我望着那棵被铁栏杆围起来的古松,想象着三百年前,那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挥锹培土的场景。那时的大清帝国如日中天,康熙平定三藩、收复台湾、驱逐沙俄,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序幕。而在这热河行宫,他或许暂时卸下了帝王的威仪,只是一个喜欢种树的老人家。
雾气渐渐散去,阳光透过云层洒了下来,在湖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游人纷纷举起手机拍照,咔嚓声此起彼伏。我忽然想起昨日那位摇蒲扇的大姐说的话——"不常见哩"。是啊,这样的烟波,这样的景致,确实不常见。古人所见,与我们今日所见,虽有相似,却又不尽相同。那些松树还在,那些建筑还在,但看树的人、住楼的人,早已换了不知多少茬了。
导游招呼大家集合,说要带我们去看看"热河"。我这才记起,避暑山庄又名"热河行宫",而"热河"本身也是一处奇景——一处不冻的泉水,即使在寒冬腊月也不封冻结冰,故而得名。据说当年康熙发现此处泉水温暖宜人,周围风景秀丽,才决定在此修建行宫。
热河泉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,不过是一方池塘大小,水极清澈,可以看见底下的鹅卵石。水面平静如镜,倒映着周围的古建筑和游人的身影。没有雾气,没有波澜,平凡得几乎让人失望。但细细想来,正是这眼不起眼的泉水,孕育了整个避暑山庄,乃至承德这座城市。
"这泉水常年保持在八度左右,"导游说,"冬天不结冰,夏天却觉得清凉。"
我蹲下身,伸手触碰水面,果然感到一丝凉意。这水温,倒与人的体温相似,不冷不热,恰如其分。想来康熙当年也是被这份"恰如其分"所打动吧?一个统治着庞大帝国的皇帝,日理万机之余,最渴望的或许正是这种不温不火、恰到好处的舒适。
离开热河泉,我们来到了山庄的正殿"烟波致爽殿"。这是皇帝处理政务和接见大臣的地方,名字自然取自那湖上的烟波。殿内陈设简朴,与紫禁城的金碧辉煌截然不同。导游说,康熙、乾隆在此居住时,都刻意追求简朴自然,以示不忘满洲本色。
我站在殿前,望着门楣上"烟波致爽"四个大字,忽然明白了这名字的深意。对皇帝而言,"爽"字何止是体感上的凉爽?更是精神上的放松与解脱。在这远离京城的行宫里,他们或许能暂时放下帝王的架子,享受片刻的闲适与自在。
就像今日的我,初入山庄时满腹牢骚,却在不知不觉中被那烟波所感染,继而陶醉,心境渐渐平和下来。现代人的生活,何尝不需要这种"致爽"的时刻呢?我们被工作、被生活、被各种琐事所困,心灵日渐干涸。偶尔置身于这样的山水之间,让那烟波雾气浸润身心,或许才能找回些许本真的自我。
离开避暑山庄时,已是傍晚时分。武烈河畔的雾气又升腾起来,与早晨在山庄所见如出一辙。那位摇蒲扇的大姐不知是否还在原处纳凉?我想告诉她,我确实见到了她所说的雾,很美,很"致爽"。
回望避暑山庄,暮色中已看不清轮廓,只有那高高的门槛还隐约可见。我戛然觉得,那门槛不仅隔开了山庄内外,也隔开了两个世界——外面是喧嚣浮躁的现代生活,里面则是可以暂时放下一切、让心灵休憩的所在。
跨过那道门槛,我又回到了熙熙攘攘的街头。衬衫依旧黏着后辈,但心里却装着满当当的烟波雾气,足够我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,保持一份难得的清爽。
|
|






 窥视卡
窥视卡 雷达卡
雷达卡



 发表于
发表于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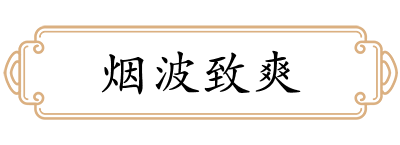

 提升卡
提升卡 置顶卡
置顶卡 沉默卡
沉默卡 喧嚣卡
喧嚣卡 变色卡
变色卡 千斤顶
千斤顶 照妖镜
照妖镜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