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|
本帖最后由 东湖岸边人 于 2025-9-14 11:12 编辑
这几日,武汉终于褪去燥热。黄昏时分,我仍坐回阳台那把旧藤椅上去。藤条硌着后背,竟也觉出几分踏实。拇指摩挲过手机屏,播音键一按,那个温和的女声便再度响起,讲述着《杨绛经典语录》——不高,不低,像初秋江风拂面,徐徐入耳。
“好的教育,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。”话音未落,楼下蓦地炸起一声嚷:“快走快走!培优班七点就上课了!”我扶栏俯看,是隔壁单元的小朋友天一。他背着的蓝书包早已褪色,肩带磨得泛白,沉甸甸地压得他整个人向前弓着,像棵才抽条就被风吹歪的小杨树。他慢吞吞地走,脚尖一下一下踢着石子,连书包滑落了也懒得抬手拉一把。
这孩子,我是看着他长大的。从前总跟在我身后,举着根芦苇仰头问:“爷爷,蜻蜓为什么要点水?”“江水为什么老是哗啦啦?”那时他眼睛清亮,像落进了星光。如今呢?那双瞳仁像是被什么磨黯了,只剩一片倦怠的灰。听说整个华中地区七成中学生每日休闲不足一小时——这哪是成长?分明是一场疲于奔命的拉力赛。杨绛先生活到百岁,若先生见孩子们这般模样,会不会轻轻叹一口气?
播音里的声音依旧平和。里面说,杨绛先生教女儿钱瑗,从不如此。上一秒在菜场指点着白菜萝卜讲植物分类,下一秒粥沸扑锅,便笑着打趣:“看,这白汽是不是也急着跑去玩?”你听,这才是教育本该有的样子——不是灌满一桶水,而是点燃一束光。何须正襟危坐?何处不是课堂?
不由得想起上周在得胜桥买菜,卖藕的老王正捏着一节断藕对孙女说:“瞧,丝还连着,这是它的脉,水就从这里流过。”小女孩踮着脚伸手去摸,泥点沾上指尖也浑然不觉。她妈妈催她回家,她却仰头追问:“那莲蓬是怎么怀上莲子的?”——市声嘈杂,吆喝声、车铃声、馒头出笼的蒸汽氤氲缭绕,可这一方小摊前,却仿佛有个无声的课堂正在生根发芽。没有黑板粉笔,鲜活的日子,本就是一部教科书。
江风捎着水汽漫过阳台。我抚过藤椅微裂的扶手,忽然忆起少年时在滨湖机械厂学工的日子。师傅提着扳手,在机床轰鸣中指着齿轮说:“齿要对准,差一丝就全废了。”这场景,隔了半个世纪,竟与杨绛教女、老王说藕隐隐重合——真正的传授,不都在堂皇的厅室,也在生活滚烫的深处。想来,杨绛先生若闻此声,必会颔首微笑。
“走好选择的路,别选择好走的路。”耳机里传来这一句,像温好的黄酒滑入喉肠,暖意缓缓漾开。这声音引领着我,走向另一个时空——杨绛四十七岁决心重译《堂吉诃德》,放下早已熟练的英法译本,从头学起西班牙文,连字母都重新认读。译稿曾被抄没,又奇迹般从废纸堆中捡回——纸页泛黄,边角卷皱,她便在煤油灯下一字字修补。干校劳作日夜不息,她手上水泡叠着血泡,夜里却仍蜷在褥间,借小灯微光核对动词变位。
这般路,几人敢走?几人能走到底?可杨绛一步一步丈量过来,最终让七十万册译作走入千家万户。岂止是杨绛?褚时健七旬上山种橙,叶嘉莹九旬跨洋传诗,还有我家邻居陈老师——退休后腾出客厅,摆几张旧课桌,为外来务工子女补课整整八载。我曾隔窗听见她教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: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……”孩子们跟读的声音清亮如春水。问她累不累,她只笑:“容易的路越走越窄,难走的路倒越走越宽。”
你听,这世间总有人不拣易路而行。他们如江心礁石,任浪涛扑打,依旧岿然自立。
“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。”杨绛的这话,像块小石投入我心潭。直到前不久躺在手术台上,麻药渐侵时,我才真正懂了这话的分量。肠镜胃镜轮番探入,几十枚大小息肉被切除。吊针日夜滴答,手臂肿得发亮。可我忽然想起她——杨绛被剃阴阳头、挂牌游街时,仍悄悄把译稿塞进棉袄夹层,夜夜蜷在灯下与文字相依。那纸页上淌过泪吗?映过笑吗?与她相比,我这点痛楚又何足言道?
是了,苦难如淬火。非得烧红烧透,再猛地浸入冷水,才能炼出钢的脊梁。快乐从来不是纯粹的蜜糖,它总掺着细沙,磨得人清醒,就像武昌糊汤粉,总要配一口辣萝卜才够味。
想起2020年封城七十六天。我眼疾日重,窗外香樟渐糊作一团绿雾,连垃圾桶都成了模糊的黑斑。可耳朵却醒了:清晨志愿者鞋跟敲响楼道,脆生生的;午间张大姐喊“白菜到货啦!”,嗓门裹着热气撞进窗来;深夜犬吠一声划破寂静,像在对整座城市道晚安......
我便借手机语音慢慢记录,用指尖在屏上颤巍巍地敲。写麻雀在窗台啾鸣,写街道的路灯彻夜亮着,写李阿姨端来的冬瓜丸子汤,写外卖小哥风雨兼程送来的物品,写收音机里播报的抗疫消息,写封在家里的退休老人手机上按时响起的养老金发放铃声……我每天把心中最动人的感触写成诗歌或散文,共得一百多篇,发在朋友圈。有不少人说:“读了您写的,才觉出日子还在暖着。”
原来人即使困守一室,也可做一盏小灯。如杨绛在干校偷译《堂吉诃德》,光虽微渺,却足以照亮自己的方寸天地,亦能温暖他人的寒夜。
“人的尊卑,不靠地位,不由出身。”这句话坠进心里,漾开圈圈涟漪。我们这个时代,有人用数字丈量一切,KPI、头衔、身价如标签般贴满人生。这让我想起狄更斯笔下的葛雷梗,终日与数字为伴,却忘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。可杨绛不这般。为校一个注释,她踏遍北京图书馆台阶,托人寻遍海外孤本。她的贵气,从不来自“先生”的尊称,而源于对学问的虔敬、对真理孩童般的赤诚。
巷口修鞋的李师傅,摊子支在老槐树下十几年了。工具排列齐整如仪仗队,剪刀柄磨得锃亮如银。环卫工鞋跟磨穿,他寻来厚皮仔细缝补,分文不取。“您天天走那么多路,鞋得结实些。”阳光淌过他花白的头发,竟照出某种难以言喻的庄重。那一刻我觉得,他比许多挥金如土者更尊贵。
屈原说“举世皆浊我独清”,杨绛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?真高贵从不依托华服广厦,而是内心那捧不灭的善念与本分,如长江之水,纵泥沙俱下,依旧清澈东流。
如今读书,字常幻作蚁群游动。可耳朵竟成了另一双眼睛。听《我们仨》,仿佛踏入三里河小院:钱瑗正为父亲钱钟书画肖像,猫的胡子翘得老高;母亲杨绛织毛衣的针儿咔嗒轻响;阳光溜过窗棂,泊在书页上暖洋洋的。听杨绛讲《斐多篇》,又似置身古希腊广场,苏格拉底与弟子论辩灵魂不朽,风里漫着青草与智慧的气息。
从前总以为读书须正襟危坐,字字目接。如今才懂,读书原是一场心对心的聆听。目虽昏花,心却愈发明亮,如江滩灯火,白昼隐没,夜色一临便照彻征途。
每至暮色四合,我总爱去江滩石阶坐坐。揣着手机,戴着耳机,任杨绛解读《堂吉诃德》的嗓音混着江涛淌入耳中——涛声激越,语音温软,奇异地交融共生。
眼前长江大桥车流如灯河奔涌,江汉关钟楼时针缓移。九点整,钟声“咚——咚——”荡过江面,携着水汽拂面而来,凉丝丝沁人。
掌心贴紧石阶,能触到江风送来的湿凉,能听见浪扑堤岸的节律,更能感知耳机里那把温和嗓音如耳语:“慢慢来,别急。”
我忽然了悟:真从容非如顽石寂然不动,乃如江心航标灯——任浪涌风狂,始终亮着那簇光。杨绛先生离去已九载,可她的声音从未远走。她化入一缕江声、一记钟声、一阵武昌老巷的微风,日日在两江四岸回旋缭绕。
涛声依旧拍岸,耳机里嗓音复起。我侧耳细听,心下更豁然:人这一生,岂仅靠双目视物?更须凭心眼看世界。能看见多少暖意,听懂几分真言,守住几寸心光,生命的天地便有多宽广!
风又拂过,携来杨绛的话音与江涛絮语,在耳边轻轻道:“慢慢走,好好过。日子的真味,俱在这听、这悟、这守之中。”
|
|




 窥视卡
窥视卡 雷达卡
雷达卡
 发表于
发表于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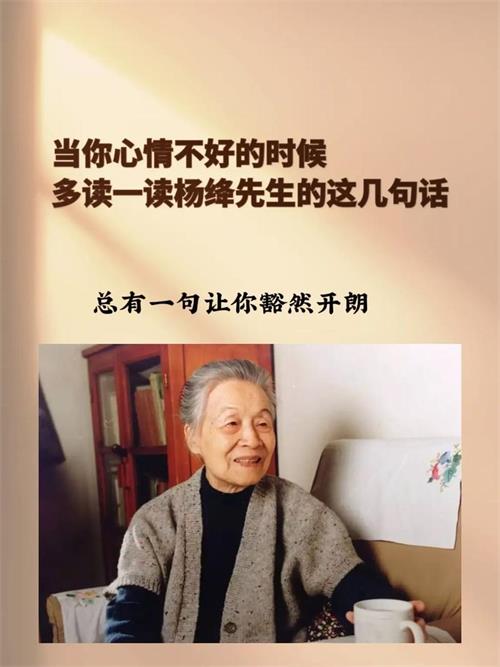
 提升卡
提升卡 置顶卡
置顶卡 沉默卡
沉默卡 喧嚣卡
喧嚣卡 变色卡
变色卡 千斤顶
千斤顶 照妖镜
照妖镜






